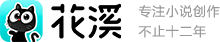北京沙梦
- 已读 56%
- ( 42/ 75)
002120
驶往上海的列车即将起程。
“祝你马到成功!”盂来章握着杜需沙的手说,“等你的好消息。”
杜需沙闪了几下眼睛,马上说:“这一会我编了一句谜语诗:马陵道间无碑墓,去证光复台湾人。打一成语。马陵道,去中间的陵字,郑成功,去掉第一郑字,就是你说的马到成功呀。一旦成功,我把这句拍电报给你。”
“你也应该有万一不顺利的准备。”
“那电报上我就会写:今日已到黄浦滩,可告江水之颜色——黄了呗。”杜需沙说完,把盂来章的手用力一握,充满自信地说:“我一定会成功的!”
对盂来章,杜需沙内心的感受从不隐瞒。他总是向别人介绍着盂来章说:“这是最好的朋友!他是我人生中交的第一个朋友。”当年,杜需沙和盂来章一起从同一个小学升到一一一中学,所在年级的学生来自两个不同小学。不久中学召开田竞运动会,在瞩目的一百米短跑项目上,所有人都关注着杜需沙与李海两个人,大家都知道,他们是不同两个小学中跑得最快的人,以前还未曾同场分过高下。年级里大多数的学生来李海原来的小学,他们前呼后拥着李海,都说李海奔跑如飞,一定能够赢,包括李海小学同学的周燕诚。当同学们探询杜需沙的时候,无论他们是支持自己还是支持李海的,他都平静地大声说:“李海跑得真的非常快,我看见过他训练。我最近腿上有点小伤,只能够自己尽力跑好得好些。”他却私下对感到焦急的盂来章低声说:“我一定能够赢李海!李海跑得比我快?那都是他们说的,不是跑出来的。我现在状态好极了,你就等着看吧。”比赛结果:杜需沙把李海甩在身后三、四米。周燕诚后来告诉杜需沙,他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看着远去的列车,盂来章的心里对杜需沙更加充满敬佩。他与杜需沙从小在一起朝夕相处,一直感受着杜需沙的与众不同:勇敢、成熟和自信,让人意想不到种种的神奇。
有一次放学后,杜需沙到他家里玩,他问杜需沙:“为什么你脑子里总有那么多奇怪的想法呢?一件同学们眼里很普通的事,你却能说出一大堆的感受。”
“你也有。只是你没有发现。”杜需沙回答。
“我没有,我真的没有。”他认真地说。
杜需沙把他拉到窗户前面说:“你就站在这里,向外看!”
盂来章看着窗外,莫名其妙地说:“看哪里?”
“随便你。”杜需沙走到他身后,也去看着窗外。
“没有什么呀。”他笑着回头说。他家窗外的一切,十几年来都没有改变过,已经司空见惯。
“别说话,你多看一会。”杜需沙仍然站着,动也不动地说。
过了几分钟,杜需沙问:“你看见什么了?”
“烟囱。我们家窗户外,最明显的就是眼前的这个大烟囱了。”他回答。
“你再继续看,向远看。”
过了几分钟,杜需沙问:“你看见什么了?”
“夕阳。”他回答。
杜需沙不做声。
过了几分钟,杜需沙问:“你看见什么了?”
“夕阳在下沉,路上人在走动。”他回答。他看见,橘色的夕阳如盘,一点一点地在天际下落,天空开始灰暗,街上的行人,无言地匆匆行走……。
“你刚才有什么感觉吗?”杜需沙问他。
“感觉?刚才,有一阵子,心里突然感觉……我说不出。”他沉吟着。
“你说不出的是高兴?难过?还是其他?”
“好像都有点吧。就像自己突然丢了什么东西……,说不清楚,反正有点怪怪的感觉。”他思索着。
“来章,这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呀!”杜需沙告诉他。
雨滴打在车窗上,车窗蒙着水雾,车窗外漆黑茫茫。硬座车厢里鸦雀无声,只听到列车轮子轧着铁轨的声音,机械、单调和反复。灯光刺眼,周围的乘客已经疲惫地睡着:或俯在桌上,或者头靠座背,或东倒西歪的。杜需沙抱着胳臂坐着,始终毫无困意,心绪翻滚。
列车在雨夜中飞驶,像无可阻挡的钢铁巨龙,离背后自己所熟悉的一切,越来越远,而距前方自己所陌生的未来,越来越近。有些害怕,有些欣喜,有些依恋,有些渴望,杜需沙身体微微发着抖,眼眶里充盈着泪水。像一个赌徒,变卖了自己全部的拥有,只身来到一个神秘的赌场,忐忑不安,面对一个高贵的女皇,押上所有的一切,去赌一把未来的人生,答案即将揭晓,女皇高高地端坐着,笑而不答。
杜需沙突然感觉到,胸中竟然充满了悲壮——如同荆轲身临易水一般。
经过整整一夜,列车在清晨到达了上海。杜需沙一走出火车站,迎面扑来湿润的空气,他大口地呼吸着,感到上海与北京这两个城市极大的不同,这里让他耳目一新。北京如一个身穿笔挺中山装的中年人,面孔摆着庄重,又流露着玩世不恭,上海像一个身穿别致西装的年轻人,仪表充满朝气,又渗透着小家碧玉,然而,这里更具有着活力。建筑——即使是颇为破旧的,多姿多样,蕴涵着风情;人们举手投足间充满着情趣:柔和的讲话,得体的穿着,骄傲的情态,快速的行走。
对许多北京的男人来说,上海女人比上海城市本身更有吸引力。文雅的上海女人,具有一种特别的气质,从袜子口或衬衣领子的花边就可以感受到,即使并不漂亮的女人,也很会打扮,表现着娇滴滴。妈妈过去总在说:上海女人会过日子,比如文贞阿姨,收入不高,却把家庭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文贞阿姨烧的菜比自己家的可口,文贞阿姨说话声音很轻,文贞阿姨衣装与众不同,她总是自己裁缝,从不穿大红大紫,即使是素白粗布的连衣裙,腰间点缀着蓝带子,胸前砸着网眼花饰,充满韵味。
杜需沙觉得有东西在碰他。一个带着红袖标、吹着哨子指挥行人的老头,正用手里的一只红旗竿子敲打着他的书包,并在说着什么。他虽然听不懂老头讲的上海话,但是明白老人在提醒他:小心小偷。
他书包里只装着一件红色的毛衣、一件白色的衬衫和一个大信封。毛衣和衬衫是他看遍自己所有衣服后才决定带来的,为了保持衣服的干净,在列车上他没有穿,身上是一件平常日子穿的运动衫,套着灰色西服外套,为了不让西装出皱,他在列车上一路端坐,结果冻得他身体冰凉,浑身发酸。大信封里装着厚厚的信纸,写满了他要对鞠雨文说的话,他知道,自己在表达能力方面口头逊于文字,还有,许多话通过文字形式的表露更合适,最重要的一点:当他见到鞠雨文后,心情发生的波动是能够让他言语和思维平静,所以他就用了一夜的时间,写好了这封长信。
当他下了公交汽车,终于找到上海医学院大门的时候,他躲在门口的树旁,换上了书包里的衣服。然后,一路打听,来到了鞠雨文宿舍门口。
“打扰一下,请问鞠雨文在吗?我是她北京的同学。”杜需沙一边说着,一边迅速地扫视着里面的两个女生,与脑海里鞠雨文模糊的影像比较着。
两个漂亮的女生人都长得干净,相互看了一眼,一起说:“雨文在洗澡。”
矮个子的女生笑吟吟地说:“我去叫她。”就跑出去。
高个子的女生客气地说:“请进寝室里坐吧。”
杜需沙感觉到高个子女生不住地在打量着他。高个子的眼睛,如同大多上海女人一样,大而略为干涩,带着尖锐的目光。
“你从北京来的吗?”高个子女生问。
“是呀。”
“你是雨文什么时候的同学呀?”
“中学的。”
“哦。以前你来上海找过雨文吗?”
“没有。我第一次来上海。”
“你这次就来是看雨文?”
“我是出差,知道雨文在这里读书,顺便来看看。”
“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?”
“在北京的一家计算机公司。”
“你的西服很漂亮呀,是进口的吧?要几百块吧?”
“我的西服?北京产的,很便宜,六十块钱,还包括一件裤子呢。”
正聊着,矮个子女生跑着回来了,兴奋地对杜需沙说:“回来了,雨文来了。”
接着门口出现了鞠雨文。
如果是在大街上,杜需沙绝对不敢辨认面前的这个人是鞠雨文,她变化实在太大了:个子长得很高,戴着白色眼镜,脸似乎比过去宽了些,端庄的神情——就像医院里的大夫。再仔细去看,才能看出过去的影子:清纯的脸,略微瘦弱的身材,小心翼翼的姿态,谨慎的目光。
“我是杜需沙。”杜需沙马上自我介绍着。
“唔……你好。”鞠雨文眼睛眨动着。
“一一一中学……”
“哦!你好呀。”鞠雨文露出微笑,“我去给你倒点水喝,一路很辛苦吧。”
旁边,矮个子女生满脸是笑地看着他们,高个子女生已套上了一件白毛衣外套,显得楚楚动人,不做声地收拾着什么。矮个子女生去拉高个子女生,“我们去教室吧,让他们聊。”
鞠雨文对于杜需沙的造访,的确很吃惊,同时也有一些兴奋。自从她离开北京到上海读书,大学生活已经将近六年,还没有同学来找过她。以前,从天南地北来过的人,都是其他女生的同学或者朋友,今天突然有自己的同学来到,她不免有些紧张,鼻子上微微有了汗珠。她用自己纤细的手指,像拿手术刀一般地用水果刀削着苹果皮。
“我在回来的路上还想,咦!有中学的同学找我?是高中实验中学的?能是谁呀?”鞠雨文用手指向上推了一下眼镜,“真没想到是一一一中学的。时间那么久了呀。”
“你不记得我了吗?”
“你的名字,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;你的样子,我可真想了半天呢。我记得过去你眼睛总是眯着,好像永远睁不开似的,怎么现在突然睁开了,变大了。”
两个人聊着:彼此简单的情况,过去的同学和老师。
杜需沙看到已经中午,便说:“我还有事情,先走了。”
“我们一起到学校餐厅去吃饭吧,那是专门给来校客人准备的餐厅,菜烧蛮好的。”
“谢谢了,我确实有事办。我要去华东工学院看一个朋友,他在哪里读研究生,也是很久没有见过面了。”
“哦。你看,你那么远来的,不吃就走,多不好意思。”
“我明天晚上回北京。明天白天有时间,希望临走前请你吃顿饭,一起聊聊天。不知道你明天有时间吗?”
“哦……”鞠雨文略微沉吟了一下,“好呀,现在是假期,有时间。那你明天来寝室找我吧。”
“明天早上八点,我在你们学校大门口等你吧。这毕竟是女生寝室,我觉得会不太方便。”
“那也好。”
鞠雨文送杜需沙出了学校门口,微笑地准备告别,杜需沙突然将信封交到了她的手上,“这个给你。”
“咦!这是什么?这是什么呀?”鞠雨文如神经质似地身体哆嗦了一下,信封差一点掉到地上,脸露疑惑,眼光警惕。
“我写的东西,你拿回去看看。”
“这?”
不等鞠雨文再说什么,杜需沙说着“明天见!”转身快步就走。鞠雨文捧着沉重的厚信,一头雾水。
杜需沙与上海唯一朋友罗平,竟然已经有十一年没有见过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班里来了一个从上海到北京探亲戚的借读生,他穿着瘦腿的裤子、梳着分头和称我为“阿拉”,大家叫他“小上海”,他就是罗平。罗平的亲戚与杜需沙的爸爸是同事,就住在杜需沙家附近,他喜欢读书,懂得也多,于是很快就与杜需沙成为朋友,被杜需沙认为是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朋友。罗平只在北京读了一年书,就回到了上海,但是他们两个人始终保持着通信,信里都是自己胸中的万丈激情、相互友谊的钢铁誓言和彼此未来的美好憧憬。那几年北京男孩子流行穿白色边的布鞋,只有上海能够买到,罗平每年总会给他邮寄一双。
即使是在华东工学院读研究生的罗平变得很大,两个人相见后一点没有陌生感。在学院的餐厅里,罗平请他吃饭,两个人都觉得很亲切。杜需沙如实告诉了罗平来上海的目的,罗平听完后说:“杜需沙就是杜需沙呀。”
“你没有交一个女朋友吗?”杜需沙问。
“没有呀。我还没有目标,不如你老兄心明眼亮啊。”
“是不是看花眼了——上海女孩都个个如花似玉的。”
“我告诉你,上海的女孩不如北京的女孩。”
“北京的女孩怎么好?”
“大方,开朗,特别爽快。我去过北京,知道的。”
“哈哈!你才在北京呆过一年,你不了解北京女孩呀,北京女孩身上的那些粗俗你没有领教过。”
“那你说上海的女孩怎么好?”
“有气质,温柔,贤惠。”
“哈哈!老兄呀,你才根本不了解上海女孩呢!上海女孩只讲实际,自爱得过分,你不知道的。”
“哎,哎,我说罗平,不要叫这么多菜,咱们两个人吃已经足够了。”看着服务员上到第四个菜盘,杜需沙制止着,“太多了,不要了,不要了,要不浪费了。”
“只剩一个汤没有上了,其他都是一些肉炒青菜,你多吃点。”说完,罗平招呼着服务员说:“把我们点的菜快一点上齐,好不好!”
服务员答应着进了厨房。不一会,另一个服务员端来了一盘红烧鱼,放在桌子上。杜需沙未及说话,罗平脸色已经很难看,他用上海话对服务员训斥起来。服务员看了看手里的菜单,马上用上海话道歉,把那盘红烧鱼端去另一桌。
听到罗平计划明天带他去上海游玩,杜需沙忙用坚决的口吻告诉罗平,自己明天要见鞠雨文,这可是大事呀。同时,杜需沙深切地感到了罗平的诚意。
“你不像一个上海人。”
“哦?上海人怎么了?”
“恩……”杜需沙支吾着。上海人小器,他耳熟能详,在北京、在他周围,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讲,但他没有亲身体验。
“其实,上海人中像我这样的人很多。呵呵,我知道好像全国各地的人对上海人印象都不好,也许上海人做事情有很多不好的地方。不过哪个地方都有不怎样的人,要我说,你就不像一个北京人。”
“啊?北京人怎么了?”
“北京人很自大,都放不下皇城脚下第一臣民的臭架子,我同班的几个北京的同学就这样,没有一个像你这样谦和。”
两个人不禁呵呵笑起来。
晚上,杜需沙住在罗平的宿舍。他久久不能入睡,想着明天的事情,就像一名囚徒在牢里,等待明天法庭的宣判一样。


 上一章
上一章
 目录
目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