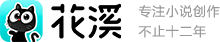金风细细
- 已读 58.33%
- ( 7/ 12)
第七章 舌绽莲花
一早,扬州大明寺的僧人,便来到府衙前,接了天师师徒一行。几位布衣僧人、十数位玄门弟子,一顶软轿,慢悠悠在青石板铺成的街市上行走,约大半个时辰,便到大明寺所在的西郊。
扬州大明寺,素有淮东第一寺之称。占地甚广,依山面水,端是的好风景。山门巍峨,殿宇高广,九层栖灵塔高入云天,一派名寺风光。山门两边站满了围观的民众,却不见方丈慧远的身影,只有知客僧了行领着数位僧人迎了过来。
天师身后的十数位弟子,均露出不悦的神情,毕竟天师身份贵重,掌管天下宗教。大明寺虽是大寺,方丈慧远固有大名,又岂可和当朝天师相比?如今避而不见,估计是有意给天师难堪。毕竟静虚天师,年纪尚轻,统管僧道二宗,难免有人不服。数千年来,佛教和道教一向分庭抗礼,甚至兴盛过道教。自大康立国后,忽曲居道教下位,自然多多少少会有令人不快的小动作。
静虚天师走出轿子,面色无波,不见一丝不悦。倒是围观的民众忽睹仙颜,发出惊呼声。
了行合什行礼,弯腰道,“天师远道而来,方丈已在大雄宝殿等待多时。天师请!”
进了大门,便是香烟袅绕、飞檐走角的大雄宝殿。大明寺主持方丈慧远带着数位寺中高僧守在大雄宝殿门口。似乎无意让天师一行进入。
静虚天师还未有表示,身后的大弟子玄明忍不住问道,“慧远大师拦住殿门,不知所为何事,如果有所打搅,我等就此回京就是。”一众弟子也是一脸怒色。
玄明是静虚的第一个徒弟,拜师前,已经在玄学上小有名气。深感所学不得究竟,后来拜在当时年仅十四岁的天师门下。精通诸家经典,聪慧持重,术法高强,是天师的得力弟子之一。皇上亦亲赐冲和真人的称号。身份比之慧远,只高不低。
慧远展眉一晒,不理玄明。却从僧袍中取出一物,捏于手中,问道,“敢问天师,此物是死是活?”
众人定睛细看,却是一只活生生的小麻雀,被慧远紧紧捏于手中。挣扎着,却怎么也挣不脱慧远的大手。
据说,这个问题前晋时也有人向当时的禅宗五祖僧灿问过。时僧灿闭目半响,回道,是生是死,均在施主一念间。那人甚服离去,五祖之名远播。
而今老话重提,却不知道天师如何应对?对于慧远来说,天师若是答不了这个问题,便进不得大雄宝殿,进不得大雄宝殿,便是输定了。也算是灭灭道教的威风。
静虚天师自然不会拾人牙慧。淡然道,“上天有好生之德,天道有数,岂是大师能决定的?”话未完,慧远手掌大张,众人尚未回过神来,那小麻雀已然振翅高飞。
慧远老面一黑,只知道有刹那间,心神完全不能自主。手掌一开,那麻雀就高飞远去了。是妖术,还是神异?难道天师真是在世神仙?
众僧眼见慧远面色忽红忽黑,脸有惭色,忙闪开让路。天师的弟子自然是面有得色,仍井然有序地进入大雄宝殿。大雄宝殿后,尚有一后门,出了门,穿过几座殿堂、回廊,便到了方丈所居的禅房。说是禅房,却是一进院落。四四方方的天井,数间明堂大屋。
居中的大厅,已经坐了数位高僧——镇江清山寺长老释道一、杭州灵观寺的主持智永大师、律宗名宿济和长老,禅宗宗长月见禅师,天台宗的大慈法师,俱是江南佛教领军人物,此刻均是低眉敛目,手持佛珠,正襟端坐。只是神色间,难掩倨傲之色,毕竟他们自幼刻苦修行数十年,才得今天之名声地位。私底下均以为天师只是依仗着出身好,真才实学只怕未必,虽世传天师神仙中人怕是无知愚民言过其实,是以难以对天师信服。
知客僧对天师道了一句,“请。”又拦住跟随的天师道弟子,“诸位道友,请随贫僧到偏殿喝茶。”
玄明等见天师没有反对,即跟着知客僧离去。
天师步入大堂,居中而坐。和诸位高僧一一见礼、寒暄过,即刻步入正题。
众高僧中,以天台宗的大慈法师年岁最长、德高望重。法师自幼出家,学行精严,通晓大、小乘经典,以讲习为业,广开法门,弟众数千。
大慈法师道,“生死事大,无常迅速。久闻天师灵根慧骨,何不深研究竟之法,而着意于拖尸带骨之学?岂不可惜乎?”佛教人士多以本教为正宗,除此均为不得究竟的外道。大慈法师心中,自然亦是如此之想。
“拖尸带骨?”听得大慈语中多有贬低之意,天师淡然而笑,“末学缁流,往往讥我道门为拖尸带骨,真是以管窥天。岂知我道家精修妙练,到那形神俱化之时寥寥太虚,但见紫光玄气,充满于天高地厚之间。明则为日月,锐则为雷电,鼓荡则为风,润泽则为雨。寻声救苦,无感不通。握大造之枢机。为众生之父母其所造,岂不光明俊伟哉?”
他这一番言论,振振有辞,随口道来,诸僧竟是无语。
又向大慈询问,“敢问法师,何为究竟?”
“所谓究竟也,解脱生老病死之苦,不入轮回。世间唯我佛四万八千法门,可得究竟,除此,俱是外道。”月见禅师见大慈面有赫色,仗着口齿伶俐,代为回复。
“若是有一人,复有生老病死,可算解脱?”天师不动声色地问。
“自然不算。”
“若此人创下的法门,可算解脱之法?”
“自然不算。”一众僧人答得分外干脆。
清玄天师饮了一口茶,见得他们已上了道,笑道:“却有一人,本是异邦小国之王子。年青时为脱离生老病死而出家。结果,出家后经历病痛、苦难、家破国亡、朝不保夕、流离失所,晚年竟因食了不净之食得了痢疾而死。诸位认为其人得究竟否?”
说到此处时,众僧均现尴尬之色,若说得了究竟,竟推翻先前之论。若说不得究竟,可是这个不得究竟的人,竟和佛祖的经历一般无二。否定其人,自然就否定了其所创之教,则众僧不如回家卖红薯算了,还有何资格坐在此处谈玄论道?
众僧脸现灰败之色,有的低首,有的汗颜。便是以辨才无碍著称于世的月见禅师也无言以对。唯清山寺的长老释道一喝斥道,“荒谬,我佛如来早证大道,脱离轮回。真身涅槃,不生不灭。逝去的只是佛的应化身。”
“哦。你说是便是了。”静虚天师淡然相应,倒不多争。反是释道一面有惭色。
“阿弥陀佛,”大慈法师垂目道,“天师果是有道高士,既是如此,何不放下一切,专志清修,早证大道?”大慈自知辩论不过,却暗讽天师着意荣华,舍不得放下名利权禄。
“若欲放下,必有所得。敢问大师,天下间哪一样,是实实在在为我所有呢?别说名利,便是这俱身子,将来也是尘归尘,土归土。最后还能留下什么?”
“这,这,”大慈面对反问,心念电转,终是答不上来。
“既无,又谈何放下?”一室俱静,只听到天师淡然的声音。


 上一章
上一章
 目录
目录